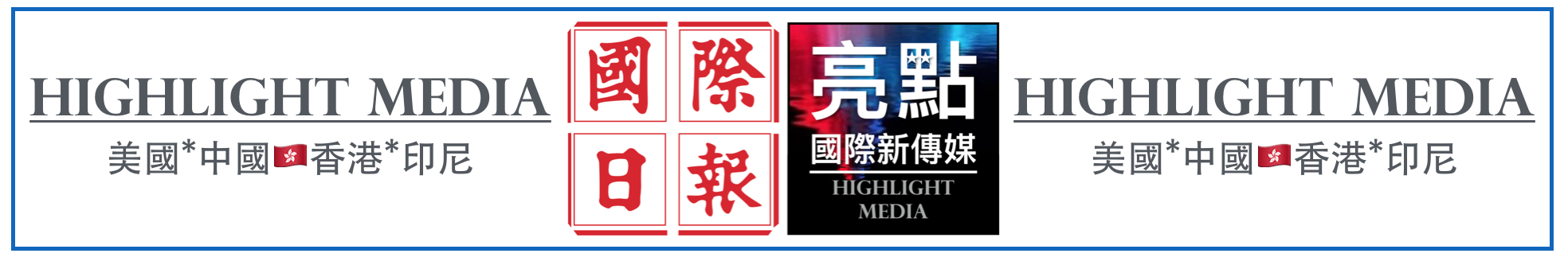 庫爾班江:讓大家看到一群真實的新疆人
庫爾班江:讓大家看到一群真實的新疆人
其實新疆人和北京人、上海人、山東人沒有什麼兩樣
在北京南禮士路附近一家僻靜的咖啡屋裡
庫爾班江·賽買提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說

【國際日報訊】庫爾班江·賽買提這位出生在新疆和田的維吾爾族攝影師,在他32歲那年,突然成了中外媒體追逐的焦點。 2014年10月,他在自己的新書《我從新疆來》裡,圖文並茂地講述了100名在內地工作生活的新疆人的故事。這些書中的主人公包括維吾爾族、漢族、哈薩克族、錫伯族等十幾個新疆的主要民族。
眼下,同名系列紀錄片正在熱拍中,而這才是庫爾班江的初衷。作為書的延續,他的計劃是通過影像的力量,以最直觀具體的形式,記錄20位不同民族的新疆人的經歷,講述他們在祖國內地生活發展的故事。
“我講的故事無關乎民族、宗教、地域,就是普通人的故事,他們在默默無聞地為國家作著貢獻。”庫爾班江說,身為紀實攝影師、職業攝像師,他用書和影像記錄普通人的夢想和奮鬥。
“如果出一本書,寫100個人的故事
那影響力一定會更大吧”


在庫爾班江看來,不少外國人對新疆的認識基本上限於旅遊宣傳,連一些內地人對新疆和新疆人的片面理解有時候都讓他哭笑不得。 “一次在電視台錄節目,編導問我能否穿民族服裝,我說你眼裡的民族服裝是什麼?他們就直接給我上了跳舞的衣服,幸好沒給我手鼓。我說生活中我不是這麼穿的。”庫爾班江說,有些維吾爾族學生到內地上學,他的同學甚至會問,你們上學是騎馬嗎?
“7·5事件”發生時,庫爾班江正在蘭州拍片,看到這個新聞,“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不知不覺眼淚就流下來了,心裡非常酸、疼。這不是幾年時間能夠恢復的”。
庫爾班江有個一起長大的漢族發小,“小時候,我們天天打架,我跑步他也跑步,我練拳擊,他也練,他練不好我就打他,那時我們都沒有覺得誰欺負誰。我們一年不通話,但每次我回和田,他都會第一個出現在我面前。他大學學的是維吾爾語,因為他覺得我漢語不好,需要用維吾爾語和我交流。”這段經歷讓庫爾班江堅信,只要建立起一種長久的溝通方式,任何誤解都會被消除。
庫爾班江說,新疆和內地一樣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發生了巨大變化
庫爾班江覺得該告訴周邊的人
現在的新疆是什麼樣子
《我從新疆來》的選題早在3年前就有了。最初庫爾班江想拍的是紀錄片,拍10個人,每個人十幾分鐘,然後通過網絡的方式傳播,讓大家看到一群真實的新疆人。 “我想打破傳統紀錄片拍攝方式,用電影的概念、電影的手段來拍,但一算要600多萬元。當時劇組也成立了,由於資金沒到位,只好放棄了”。
紀錄片暫時拍不成,庫爾班江決定先做些前期採訪,用圖文方式展現在內地工作的新疆人的真實故事。他覺得最能改變人們看法的就是和自己同樣勤勞上進的新疆人,“如果說少數人的錯誤做法可以破壞一個群體的形象,那麼多數人的正確理解和積極行動更可以改善一個群體的形象” 。
從2013年年底開始,庫爾班江利用一切空閒時間開始在全國范圍內追踪採訪對象,並陸續在自己的微博中呈現。 2014年4月1日,首發在網易《看客》上的圖文專題記錄了30個新疆人的故事,居然有了2500萬次點擊量。這麼多人關注,證明大家迫切需要這個溝通交流的平台,這堅定了他的信心。 “如果出一本書,寫100個人的故事,那影響力一定會更大吧。”庫爾班江想。
在接下來近一年裡,庫爾班江行程數万裡,走訪了20多個城市,採訪拍攝超過500人,完成了一個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新疆不能被極端的情緒籠罩。如果我們不主動發出自己的聲音,就會有其他不利的聲音和觀點冒出,左右別人對你的看法,嚴重影響新疆人的聲譽。我願意做些實實在在的事,並通過自己的努力,向世人表達一個完整清晰的新疆。這是我的使命。”庫爾班江說。
一開始,庫爾班江先找了30多位身邊的朋友作為採訪對象,然後這些朋友不斷介紹新的採訪對像給他,“也有很多人直接拒絕我,說這樣做沒用。還有的人,反過來質疑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有意義嗎?”庫爾班江說,他曾一天飛過3個城市,有時候本來電話裡頭聊得挺好,但當他從一個城市飛到另一個城市,對方卻不接電話、不回短信了。
讓庫爾班江感動的是,大多數採訪對像對他給予支持。書中最終確定的十幾個民族的100個人中,年紀最大的92歲,最小的7歲。他交給庫爾班江的文字中,有拼音、漢字,還有英語。庫爾班江說,最長的錄音資料整理出來近4萬字,“故事太精彩了,我捨不得刪,雖然只用了其中的5000多字,但我把它當成資料,以後有機會單獨發表” 。
那些日子,他形容自己像打了“雞血”一樣亢奮。每天5點起床,凌晨一兩點到家,一天睡4個小時都是奢侈的事。有時白天採訪四五個人,晚上回到家整理照片和錄音。 “這本書是自述形式的。”庫爾班江說,這些故事沒有掩飾,沒有刻意,只是真實呈現。
“新疆其實沒那麼遙遠”
“看新聞時,新疆有時很遠很陌生;看這本書時,新疆卻很近很熟悉。這些圖片與文字裡,沒有別人,只有我們自己。這些故事出現在我們面前,本身就是改變。”庫爾班江說,主持人白岩松寫給《我從新疆來》的這段推薦語,是2014年7月的一天通過手機短信發給自己的,他覺得這是看書的真實感受。

《我從新疆來》書中所選取的100個人,有科研人員、律師、演員、大公司的總監、留洋博士、鍾情於音樂的醫生、剛到內地工作的廚師、和田玉商人,還有設計了國內多個清真寺的建築設計師、做了50多年維吾爾族音樂的漢族人……他們年齡、職業、人生經歷不同,但他們都從新疆來到內地,默默融入這個快速發展的時代,並且通過各自的努力拼搏贏得了社會的尊重。
在紀錄片《我從新疆來》的樣片裡,庫爾班江講了3個新疆人的生活和夢想:一個到北京跳舞的姑娘,一個賣烤羊肉串的大叔埃里克,一個歌手帕爾哈提。 “那個女孩每晚要跑3個場子,凌晨三四點才能下班回家。女孩打車,燈光閃爍的街頭上,所有的車不是現實世界的車,都是慢速拍攝,只有她是真實的。每個人的生活狀態不一樣,所有的人都在路上……”在庫爾班江的故事裡,對命運的關注超越了民族和地域,“大家把’新疆’兩個字拿掉,你會發現我講的就是最為普通的中國人的故事。我們也是中國公民,你所有的喜怒哀樂我們都有,我們這麼努力生活工作,只是為了做一個和你們一樣的普通人”。
有一次,庫爾班江隨攝製組到烏魯木齊採訪。有個導演沒去過新疆,一路上都在說二道橋(烏魯木齊維吾爾族聚居區)治安不好。庫爾班江就把他們帶到二道橋,然後拿走了導演的手機和錢包,讓她自己回酒店。導演後來自己找了個維吾爾族黑車司機,說錢包、手機被人拿走了,安全送達後再付錢。司機二話沒說就把她送回了酒店,卻一分錢沒收。
這些年,庫爾班江慢慢影響著身邊的人
之前不敢去新疆的,現在也敢去了
有誤解的也開始改變了態度。
“烏魯木齊是二線城市,可年輕人看到的東西和想法跟北京上海也差不多。你去那裡一看,哇,姑娘也穿得好時尚啊,也有很多國際範兒的樂隊。像我這樣的30歲左右的年輕人都在行動著,他們願意做事情,也願意出來發展。”庫爾班江說,我們都是同樣的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家庭與夢想在奮鬥。如果說我們之間有什麼不同,那也只是長相不同、語言不同、飲食習慣不同,“新疆其實沒那麼遙遠”。
來北京快9年了,庫爾班江早已習慣了內地的生活。在單位,也沒人覺得維吾爾族的他和別人有什麼不同。剛開始工作那會兒,生活上是有些不方便,但大家都很照顧他,經常是七八個甚至十幾個人出差,為了他一個人到處找清真餐廳。 “我要求吃漢餐,他們說,別開玩笑,再找找。”但他堅持進漢餐廳,經常是一份炒西紅柿雞蛋、一碗米飯搞定。
“尊重是你自己贏得的。我所拍攝的這些新疆人,他們都活出了自己的自尊。別忘了,我們也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之一,不是客人。”庫爾班江希望書中的100位新疆人的100個故事能形成一股榜樣的力量帶動更多的人,“我書中的人物都有包容、勤奮、勇敢、自信的特質,這才是新疆人普遍的品質”。

“越努力才會越幸運,越勇敢才能有改變”
作為《我從新疆來》裡第101個故事的主人公,庫爾班江把自己的故事放在了序言裡。他的故事,就是“維吾爾北漂”的勵志故事,有辛酸,更有滿滿的正能量。 “我拍攝別人,其實是在拍攝自己;講述別人的故事,也在講述我自己的故事。”庫爾班江說,這個過程當中,被採訪者的很多故事他都經歷過。
“越努力才會越幸運,越勇敢才能有改變。”這是庫爾班江為他的書總結的“中心思想”,但前提是要勇敢地走出來。 “我從和田走出來,扛起了攝像機,我一直在努力,但這個機會在哪兒那時候我不知道,當我踏踏實實做我自己的時候,這個機會自然而然就來了。”
父親說:“你們是男孩,一定要出去看看”
在庫爾班江的記憶裡
父親的故事幾乎都跟教育、知識、上學有關
和田是新疆傳統的維吾爾族地區,但改革開放不久,庫爾班江的父親因為做玉石生意開始頻繁跑內地,回來後,經常給孩子們講他遇到的人和事。父親說:“你們是男孩,一定要出去看看。”在庫爾班江的記憶裡,父親的故事幾乎都跟教育、知識、上學有關。他常說:“肚子裡面沒有墨,你怎麼能寫出字來?”庫爾班江記得小時候搬過3次家,每次都從大房子搬到小房子,直到周圍住的都是“文化人”,“我們不逃學了,學習也變好了,因為周圍的小孩都在上學”。
父親曾因生意失敗而離家4年裡,庫爾班江支撐起家裡的重擔,把弟弟妹妹送去上學。他擺過攤,賣過烤肉,做過玉石生意,面對艱辛生活始終樂觀、陽光、幽默,外出時總隨身帶著相機,拍攝吸引他的人文景象,直到遇到後來成為他乾爹乾媽的央視導演孟曉程夫婦。 2002年,孟曉程夫婦到新疆拍紀錄片,也正是那次偶遇,他們將一個喜歡攝影的維吾爾族小伙子帶進了紀錄片行業。 “孟曉程把我當成兒子,教我怎麼做人,他希望我成為一個’世界人’,而不是簡單意義上的維吾爾族人、新疆人以及中國人。”庫爾班江說,後來他慢慢理解了“世界人”的意思,“視野寬了,心胸也會寬”。
庫爾班江說,2009年畢業後,他和一個朋友在北京合租房子住。畢業第二年,一整年他都沒有什麼活兒,沒有任何收入來源,一年後才有了《時·光》,然後是《犛牛》《自然的力量》,從此以後就再沒閒下來。
“低潮的時候我也想過放棄,但最後我還是撐下來了。”在庫爾班江看來,人的潛力是通過自己逼自己挖掘出來的,“當年打拳時傷到的左眼在12年後和我開了個玩笑,在我出現一些青光眼的症狀時,剛好接到了一個去國外拍攝的任務,因為不想耽誤整個團隊的工作,一咬牙還是去了。結果在高原拍攝時,左眼視網膜脫落、穿孔,看什麼東西都是黑的,只好戴了個眼罩,以’加勒比海盜’的造型繼續工作。回來後被醫生罵,說你是不是不要眼睛了。”一直以來,庫爾班江的狀態都是“蠻拼的”,“我是一個喜歡找困難困住自己的人,然後享受那種使勁掙扎最後破繭而出的喜悅”。
2006年8月,庫爾班江以“旁聽生”的身份進入北京傳媒大學學習紀實攝影。在學校,他是名副其實的“蹭課大王”,哪個系的課都聽,永遠坐在第一排,課上問題最多。 “他們的課我都追著聽好幾遍,有的老師都’煩’我了,因為他們要說的每一句話和案例還有要放的片子我都門兒清。”庫爾班江笑道,其實那是因為當時自己漢語基礎不好,必須一遍一遍聽才能懂。直到現在他還留著當時的筆記,一共七八本,漢字、拼音、維吾爾語三合一。“北京是個競爭多大的城市啊,能幹的人多了去了,不缺拍紀錄片的,所以如果我不比別人付出更多倍的努力,肯定是要被淘汰的。我也被打擊過,比如架上機器完全不知道該拍什麼,當時導演就說’你不適合拍紀錄片’”,又是師傅一句“特別霸道的話”救了他,他說:“我說你是個好攝像,你就是個好攝像!”
但庫爾班江又特別幸運,這些年得到了不少“貴人”相助。和乾爹乾媽一起拍片,第一部參與的就是中國首部商業自然類紀錄片《森林之歌》,“拍片的起點很高”,第一次當攝像就是航拍。而且,這部片子的總導演正是師傅王路的師傅、《舌尖上的中國》總導演陳曉卿。後來,陳曉卿成了庫爾班江的“師爺”,帶著他拍了很多紀錄片,其中就包括《舌尖上的中國2》。
和作家王蒙的忘年交也讓庫爾班江受益匪淺。有過16年新疆生活的王蒙對新疆有著特殊的感情:“我喜歡新疆,也惦記新疆,可是最近老是從報紙上看到關於新疆讓人不舒服的一些事,這樣的話甚至讓很多人很緊張,不知道這新疆怎麼了。”王蒙說,庫爾班江那麼年輕,沒有任何背景,也沒有接受什麼特殊使命,但是他做了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
《我從新疆來》英文版首發後,得到海外出版界的廣泛關注,該書日文版正在翻譯過程中,按照計劃,阿拉伯文版的首發式將於今年秋季在埃及舉辦,土耳其文版的版權簽約儀式也已提上日程,“這本書的維吾爾語翻譯工作已經結束,順利的話8月下旬就可以出版了”。
“新疆那片土地給予了我們不斷努力、學習進取的性格,現在的生活和社會給了我們非同尋常又無奈的選擇和經歷,但我們的心胸就像新疆的那片土地一樣大。”關於未來,庫爾班江並不說“期待”。他說,期待越高,失望越大,最重要的是每個人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社會也是一樣,“現在就連生活、工作各個方面遇到的挫折,也覺得是幸福”。
但風風雨雨一路走過來,庫爾班江始終堅信有了理解就不會有誤解,“你心裡面想著什麼,你才能遇見什麼。只要心中充滿陽光,就一定能見到陽光。和田和新疆還有我們這個國家,都是一天比一天好,因為我相信光明戰勝一切。”庫爾班江說。
來源:香港商報全球聯盟,原創:中國青年報記者吳曉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