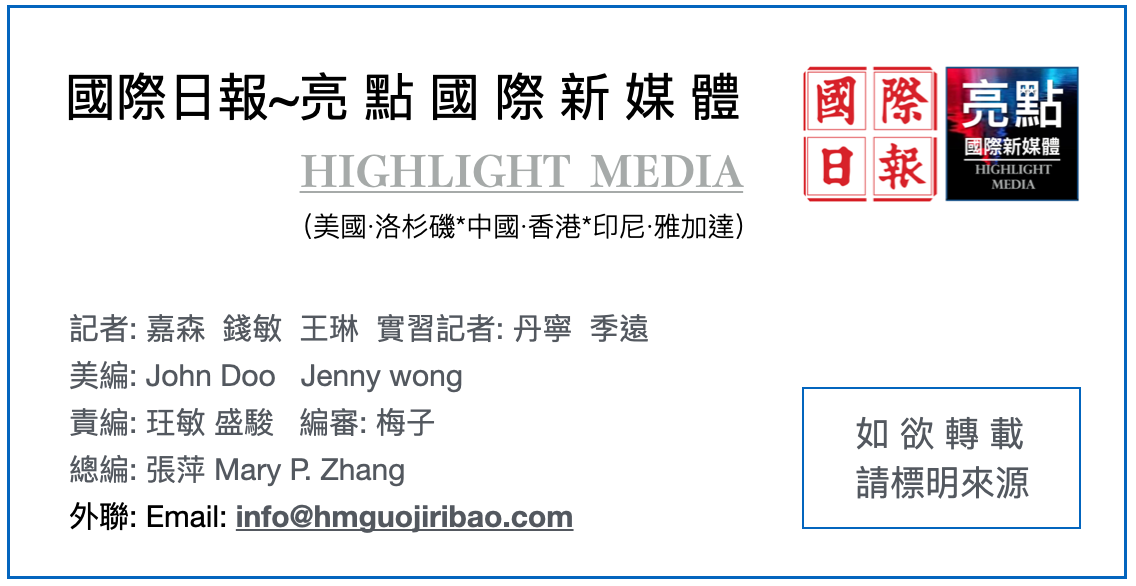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中,中國率先控制住疫情蔓延,有力改變了病毒傳播的危險進程,最大限度保護了民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藉由疫情,多方人士關注到中國國家治理的比較優勢。
疫情防控如何體現中國國家治理的特點?中西方對國家治理的理解有何差別?為什麼說國家治理現代化絕不等於西方化?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楊光斌教授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記者李純專訪,就相關問題進行權威解讀。
 資料圖:10月11日,福建省莆田市初三與高三年段學生恢復線下教學。中新社發 蔡昊 攝
資料圖:10月11日,福建省莆田市初三與高三年段學生恢復線下教學。中新社發 蔡昊 攝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應如何從這次抗擊疫情中看到中國國家治理的優勢?
楊光斌: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實踐為比較各國政治提供了百年不遇的大案例。不同國家在同一時期面對同樣的治理危機,所採取的對策不同,深刻而生動地體現了不同製度的差異性,以及不同製度在特定重大議題上的優劣,並直接通過各自秉承的治理觀念與理論而表現出來。
在這次戰疫中,表現為政策形式的中國國家治理理論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因而才能迅速遏制疫情蔓延。為了人民生命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價;“舉國體制”實現了國家與社會的合作治理,表明這個體制有強大治理能力;舉國體制和國家治理能力的深層結構則是民主集中製組織原則,民主集中製確保了製度的協調性和整合性,成為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保證。
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傳統社會治理相結合,形成了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居民自治的社會治理格局,構建了國家與人民利益一致、國家與社會合作共贏的社會善治局面。
中國共產黨的治理動員是走群眾路線,群眾路線暢通了民眾表達利益訴求的渠道,擴大了民眾的政治參與,培育了民眾的社會責任感。同時,治理主體又是多元統一,而非多中心分散的。
當代中國要努力實現的國家治理現代化,其中一個要點就在於,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國家或政府主導的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歷史表明,人民利益不會自動實現,只能由國家或者政府去代表、去努力。這是一個誰主導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性問題。
 資料圖:近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無聲詩裡頌千秋——美術經典中的黨史主題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中新社記者 田雨昊 攝
資料圖:近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無聲詩裡頌千秋——美術經典中的黨史主題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中新社記者 田雨昊 攝
中新社記者:中國國家治理的“中國性”體現在哪裡?在歷史長河中如何找到今天中國政治制度的文明基因?
楊光斌:在與西方治理理論這種強勢話語的對話中,中國人逐漸建立起具有“中國性”的治理理論,也就是國家治理理論。 “國家治理”與“治理理論”的不同在於“國家”的角色問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命題,得到各界的熱烈呼應。
這個命題被提出後,國家治理與西方治理理論就被明確區分開來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治理,本質上既是政治統治之“治”與政治管理之“理”的有機結合,也是政治管理之“治”與“理”的有機結合。在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話語體系中,“治理”是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統治與政治管理的有機結合。
對此,我們也需要注意避免兩種認識上的偏差:一是簡單套用西方“治理”概念解釋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二是簡單認為“治理”概念只是西方當代政治理論和管理理論的專利。
其實中國當下的治理體系在5000年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是有源可溯的。中國人是與生俱來的“治理主義者”,公元前8世紀中國就有了專門用於國家治理的政治經濟學,卷帙浩繁的二十四史,絕大部分內容是國家治理,不但有治理實踐的記錄,還有豐富的治理思想。
鑑於中國歷史不可思議的“延續性”,在中國管用2000多年的思想,即儒家的民本思想,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應當是中國政治思想的核心,如今中國人強調“人民至上”。
正因為中華文明基因中蘊含了無比豐富且經得起考驗的治國理政理念,比如“大一統”“官天下”“大同世”“小康世”“重農抑商”“賢能理政”“以民為本”等,這個文明共同體才得以歷經磨難而“其命維新”。這是許多西方理論家無法理解的經驗,“傳統—現代”的二分法根本無法處理中國的歷史。
中新社記者:中西方對國家治理的理解有何差別?為什麼說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絕不等於西方化?
楊光斌:雖然亞里士多德曾提出城邦的目的在於“最高的善”,但西方的現代性國家卻來得很晚,這是2000年“巨變”的結果。而中國在周朝就已經是一個統一的封建制國家,並且在這個時期已經有了“民惟邦本”的說法。
中國先賢所關注的焦點是“致治”。相比而言,希臘—羅馬幾乎沒有關於治理的思想,最高的經濟思想就是亞里士多德關於分工的觀察,自亞里士多德之後直至17世紀的西方經濟思想一直呈衰敗之勢。至於說歐洲的政治經濟學,即古典政治經濟學,整整比中國晚了200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尤其是冷戰之後,西方開始向非西方國家推行自己都從未實踐過的製度:在經濟落後、沒有法治傳統的社會強推選舉式民主即黨爭民主。
“黨爭民主”能治理嗎?必須要說明的是,“黨爭民主”能分配權力、能分蛋糕,但能不能治理則完全是另一回事。歷史與現實已經表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沒有一個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因為實行黨爭民主而走向發達序列。
西方國家的發達不是因為“黨爭民主”,而是因為發展得早。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話語,說到底是隨著其強大的物質文明而推展開來的,沒有哪一個在物質上、經濟上弱勢的國家的思想會成為世界的思想。

政黨制度、議會制度、選舉制度……這些正式的政治制度很容易模仿,有些國家甚至直接移植過來,卻依然得不到有效治理。亨廷頓用了一個詞叫“普力奪社會”,即立黨為私、執政為己,爭相攫取公共資源,這就是發展中國家非常普遍的現象。
西方人一談到治理,必然是社會中心主義或個人中心主義、多中心主義治理,強調NGO各種社團的作用,而不是強調國家的作用。由此,西方政治理論強調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去國家化、去政府化。
對世界廣大國家來說,國家治理的現代化絕不等於西方化。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把國家組織起來,對此,西方的治理理論非但不適用,甚至是在傷口上撒鹽。
實踐表明,移植而來的“飛來峰”式政治制度,會因水土不服而導致無效治理甚至國家失敗;而根植於本土的政治制度,具有民族精神的支撐和文化傳統的滋養,因而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有助於避免一個大國犯顛覆性的錯誤。
中新社記者:我們應當如何解釋“中國道路”?未來中國國家治理之路應當在哪方面予以完善?
楊光斌:中國道路可以有很多層面的解釋,但我認為其中有一個重要的邏輯是以民本思想來包容吸納世界優秀文明成果。中國自古便是民本主義所表現出的國家主義,這是我們自己在文明基因上的一項優勢,包含著組織學原理,大家稱之為外儒內法的組織學原理,講的是怎樣把國家組織起來。
國家組織起來以後,就是民本主義的治國之道,民本主義就是自上而下的國家主義。這就是說,中國人講治理肯定是國家治理,剛剛也談到了“國家或政府主導的國家治理體系”,當然這並不排除社會治理,比如說NGO的自治、村民自治等。
從過去到現在,中國政治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遺產就是協商政治。與西方的票決機制不同,中國更加重視協商民主,建構了多種協商渠道,凸顯有事好商量、一起商量著辦的人民民主真諦。
另一方面,中國也不會置身於世界政治之外。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就開始向西方取經,意圖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中國,最後則是馬克思主義勝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固本革新中獨樹一幟,“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引起世界的關注和研究。
中國人常說的“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既體現了權威—民主—法治的動態平衡,也直接表現在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上,其比較優勢已經得到證明。
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並非生搬硬套“西方化”。也正因此,中國在邁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經濟社會上的發展已有目共睹,但理論上的發展依然需要克服一個巨大的挑戰。要進一步彰顯中國的製度優勢,事關權威、民主、法治的政治理論和製度安排,還需要在政治理論上得到豐富,在實踐中得到進一步完善。 (完)

受訪者簡介
楊光斌,博士,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中央馬克思主義工程首席專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09)。發表中英文論文200篇以上,政治評論150篇左右,專著11本。近些年,在政體理論、民主理論、政黨理論、國家治理能力研究、合法性理論等一系列基礎理論研究上,取得重大原創性成果;並將基礎理論研究的成果轉化為實踐性政策,為建設中國政治話語權作出了一定的貢獻。提出並推動的歷史政治學,被認為是中國政治學發展的新範式;推動的世界政治學是國際問題研究的新議程,引領國際關係研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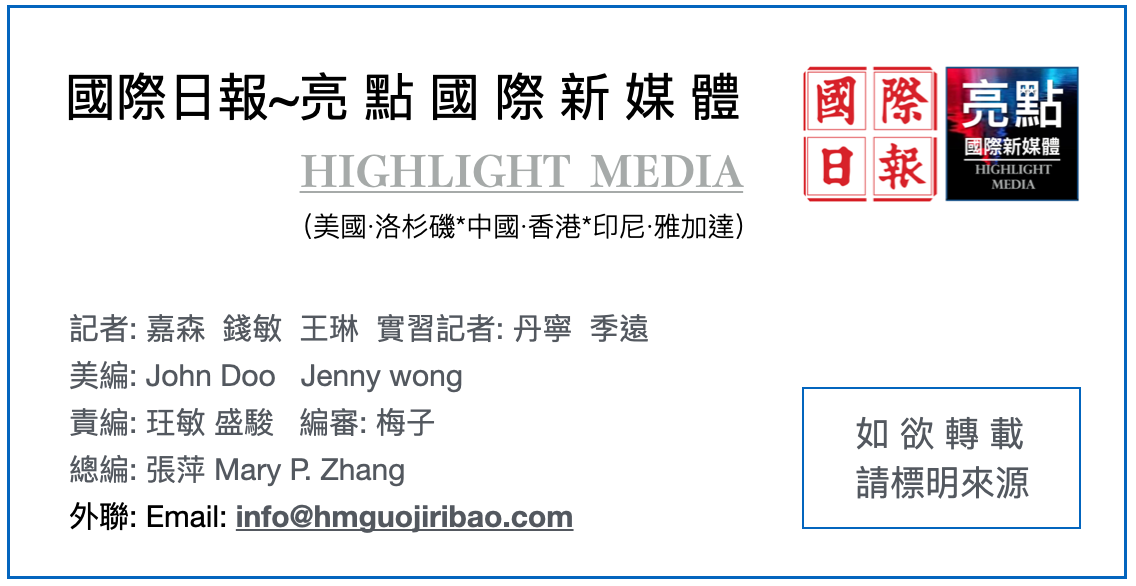





 資料圖:10月11日,福建省莆田市初三與高三年段學生恢復線下教學。中新社發 蔡昊 攝
資料圖:10月11日,福建省莆田市初三與高三年段學生恢復線下教學。中新社發 蔡昊 攝 資料圖:近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無聲詩裡頌千秋——美術經典中的黨史主題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中新社記者 田雨昊 攝
資料圖:近日,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無聲詩裡頌千秋——美術經典中的黨史主題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中新社記者 田雨昊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