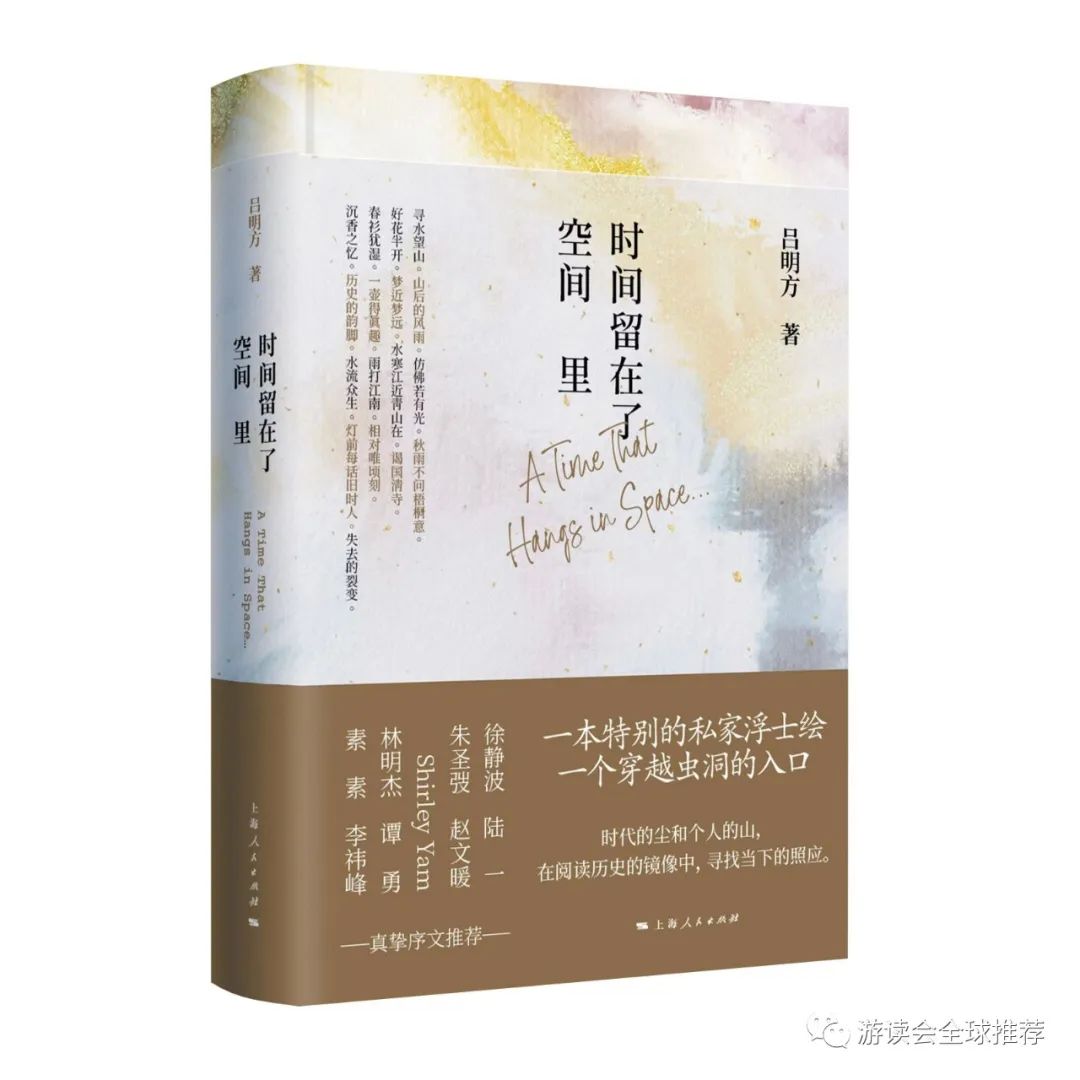
作者:呂明方
上實控股前CEO
上海醫藥集團前董事長
方源資本(亞洲)合夥人
在令人懷念的80年代後期,讀到葛兆光先生的《禪宗與中國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第一版,定價2.45元)。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國文化史叢書(周谷城先生主編)的其中一本,余英時先生的《士與中國文化》也是其中一本。這本書當時的影響很大。出版時距離先生從北大畢業僅4年,時36歲。雖然先生之後也認為寫得還是粗疏,“有一個念頭始終困擾著我,甚至可以說像一個夢魘在糾纏著我,就是如何修正我那本《禪宗與中國文化》的過分情緒化,觀念化的立場和視角。這並不是‘悔其少作’的意思,那個時代思潮所籠罩的人都會受到那種焦慮的影響,既不必後悔也毋庸諱言。”然而正是這本書開創了先生對於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獨特一頁。時隔8年之後,先生有了再寫《中國禪思想史》的動機之一。
之後讀到了先生1998年4月出版的《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紀前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和2000年12月出版的第二卷(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當時一直期待是否會有第三卷。先生說曾經有過計畫,但是沒有繼續。在學術領域,他顯然非常謹慎。一次,許知遠問過先生,“好期待。我覺得您還是應該把它寫完啊。”先生搖搖頭,說“不行啊,寫不下去了,我現在電腦裡還有好多稿子是當時寫第三卷留下來的東西,都有十幾章。可是寫不下去了。我們……”
先生在第一卷的後記中寫道,“當我寫完這部書的時候,我一點兒也沒有輕鬆的感覺,只覺得疲憊,一種仿佛要將丹田之氣都耗盡了似得疲憊。翻開日記,發現從1994年11月開始動筆,幾乎用去了三年的時間”。
“我曾經有好幾次在腦子裡閃過同一個念頭,就是對使用‘第一卷’三字的後悔,因為有了第一卷必然就有‘第二卷’,我不是只寫上卷不寫下卷的胡適之,那種只顧開闢新領域的氣派我學不會也沒有資格學,所以寫著寫著就只能暗暗叫苦,實際上,打一開始,我就有些力不從心的感覺。好在,第二卷還是在三年後寫出來了。”這時,他正在比利時的魯汶大學,正好50歲,知天命之年。
後來看了許知遠《十三邀》節目與先生的一集訪談“站在歷史的遠處”。這本紀錄片拍了2年多,從疫情中的東京上野到先生早年插隊落戶時的貴州凱裡。“學歷史的人是轉到背後去,看你卸妝以後是怎麼樣。”我和先生說,這集訪談的影響很大,甚至比他的一本書影響還大。先生笑笑,說本不想做這個節目,但是和許很熟,那時,許也在東京,說做吧,於是就答應了。
今年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再修訂版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10世紀》(定價128.00元)。從1995年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初版,到2008年的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今次的再修訂版,“這也許是我少有的,至今還不那麼慚愧的著作之一。”我從網上訂到的是2022年7月的第二次印刷版本。我讀的很慢,卻也益加敬重先生的學識與思想。
余英時先生與葛兆光先生深交,互相欣賞。2022年7月31日,余英時先生逝世一年之際,臺灣聯經出版主辦“回到余英時的客廳”線上紀念活動,邀請了曾經在余英時的客廳與先生討論學術、思考生活的好友與知交,延續對先生的思慕,探討仍在影響後世的學思貢獻。葛兆光先生回憶說,從2009年開始,我和太太在這個客廳裡,和余先生大概談了有三十多次,肯定超過一百小時。我記得我總是在那個客廳面向院子的大玻璃窗下面,回頭就可以看到養金魚的池塘,而右手邊是放著余先生跟林海峰下圍棋的照片。
他說,記得是2012年春天,我第三次到普林斯頓大學去客座。那一年,我們不僅給余先生帶去了在他老家潛山拍的一些照片和視頻,而且我給他帶了一本自己的書,就是重新修訂過的《中國禪思想史》。大概半個月以後,在一次余先生客廳,他很認真地跟我聊起唐代禪宗的問題。聊得很多,大多數我現在都不記得了,但很清楚記得余先生接連問了好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學術界對於唐宋的禪宗跟政治史的問題討論並不多?第二個問題是:為什麼禪宗對文學和士大夫生活影響這麼大,而對上層的政治影響很小?第三個問題則是禪宗在佛教的中國化,他問:“就像你說的‘老莊化’,是不是導致了禪宗跟政治有所疏離?”這三個問題他至少問過好幾次,說實在話,這些問題我一直沒想清楚。
過了一年,2013年的冬天,我再次到普林斯頓去客座。那次余先生讓我看《論天人之際》的校樣,第二年就在聯經出版了。看了之後,我跟他討論了很多,他就跟我笑著說這是他最後一本書了,可我當時就說“那不是最後一本,你還欠了一本唐代的佛教和禪宗以及歷史的研究”,他當時笑了笑說:“我現在沒有精力,這事就交給葛兆光了”,我說我可寫不出來。我沒有余先生那種高瞻遠矚的視野,到現在也沒有能力寫出來,所以想起來也真是很慚愧。
上海疫中封城解封後,在舊時法租界的一棟老宅的小範圍聚會中,有緣認識了復旦大學日本文化中心的徐靜波教授。後來說起我在讀余先生相關的書,說到葛兆光先生,他說他與先生相熟,便請他安排有機會與先生一唔。其實並無相擾之事,只是表達敬意。
歲末冬日,與先生約好了時間。本想請先生餐聚。先生這些年甚少外交,亦不喜餐聚,故改定為學校附近咖啡見面。創智天地那地段我並不熟識。我生疏的訂了大學路上的81BAKERY。是日氣溫自北向南大面積驟降10°C以上,整日冬雨綿綿,晨起還有零星小雪,江南多地卻是大雪。我甚是擔心給先生添加麻煩。然先生特別守時,還提前了幾分鐘到。
咖啡館不大,倒也是不少人,有附近的學生在看書做題。先生戴了一頂鴨舌帽,緩步走入。我明顯感覺他有些衰老。他告訴我,他的聽力很差,今天也忘了戴助聽器出門。視力由於一次視網膜脫落手術並不成功,致右眼幾近失明,僅有一些光可見。這樣使得閱讀受到很大影響。現在很少出門,除了非常有限的必須參加的活動之外,已經基本謝絕了外面的各種邀約。
先生繼續著他的學術研究,他說要把一些事情完成。我說,是否找一個學生當助手。他搖頭,說自己從來不找學生做助手,寫作,做PPT,都是自己完成。
這樣的先生真的是越來越稀少了。那天,我們聊的不算多,他說話慢,語句簡短,但時時閃現他智慧的回答。我記住了。








